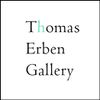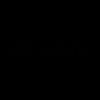柏林transmediale艺术总监克里斯托弗·甘辛的实践回望
克里斯托弗·甘辛。图片提供: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摄影:Laura Fiorio。

克里斯托弗·甘辛。图片提供: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摄影:Laura Fiorio。
自2012年以来,克里斯托弗·甘辛(Kristoffer Gansing)一直担任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的艺术总监。这一走在数字媒体与文化前沿的媒体艺术节,通过自我反思和对摇摆不定的未来的预期剖析当下时刻。对移动图像、网络文化和数字媒体的社会政治景观的探索,定义了甘辛任期内的努力,从他任上的第一届"不/兼容"(in/compatible,展期:2012年1月31日至2月5日),将不兼容视作文化生产的重要部分,到2020年任期最后一届"从终端至终端"(End to End,展期:2020年1月28日至3月1日),探讨算法操作时代中网络与基础设施的理想主义。
展览自2002年起便以柏林的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为中心地点,2020年也扩至人民剧场(Volksbühne)。媒体艺术节的形式年年不同,但核心总是说教式的话语和展陈式的项目,游走在展览、表演和工作坊之间。对于甘辛而言,一个始终贯穿其中的关键意图是强调横截性(transversatility)多于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y),注重制造往往被忽视的联系—通过举办或逐步开展座谈会、展览、电影放映会与工作坊,激发在机构新媒体实践之外更加自如的对话。
甘辛始终在处理疾速变化的当下、谨慎评议过去和展望不确定的未来三者之间保持平衡。在他的引领下,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从一个有些小众的活动变成了焦点,批评和思考那些参与了数字时代中日常生活中奇异构造的问题,而这些思考经常是超前的。例如在2012年的展览"不/兼容"里,Tsila Hassine和Ziv Neeman参与的座谈会"战争机器:礼仪与权威之间的军事科技",评议了崭新且具有显著解放性的科技如何能追根溯源到最专制压迫的指挥控制系统中—萌生自军事机构与战略的封闭世界。这场座谈会比爱德华·斯诺登披露棱镜计划早了一年。
2020年名为"从终端至终端"的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对新兴的意象提出了思考,赋予生物和数码以远在"人类"之外的复杂性—它需要一种新的调停方式,无论是通过现下活跃的抗议策略,还是将去中心化作为可实现的目标,抑或是转向循环经济的驱动力。主展览"永恒网络"(The Eternal Network)通过一系列作品,评议了在网络艺术的遗赠中正在面临的风险。Tega Brain,Julian Oliver和Bengt Sjölén的装置作品《分离》(2019),一台超级计算机对卫星、气候与地质数据进行分析,生成环境工程计划,为人类和非人类议题提出有实效的策略。
年复一年,甘辛开辟出了一条记录生命共享体验的道路,这种品质在新媒体文化的科技拜物教中时常被忽略。这一方式突出甘辛在本篇对谈中的思考,在此,他回望过去八年的变革,并展望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届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
我硕士刚毕业在大学类似新媒体的院系里工作时,就已经参加了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所以这工作经历对我而言是一种替代性的媒体教育。那时我也在做诸如tv-tv的项目,常常发现探讨数码文化和新媒体有一种极端理论和批判的方式。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则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和政治的面貌,关注的不仅是高科技媒体艺术或是与媒体产业的合作,而是放眼广阔的文化议题。这也因为它拥有较为草根和DIY媒体文化的基础,即便当时更专注于影像。这一点在2019年的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上得到呈现,我们纪念了亚历克斯·阿德里安森(Alex Adriaansens,译注:位于鹿特丹的艺术与媒体技术跨学科中心V2_. 实验室创始人)的离世。大多数站到这个台上发声的人,都谈到了他们在占屋运动(squat)等独立运动中的经历,我想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便是从这种文化中应运而生。
但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机构化,或像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这样半机构化,却仍然在某种反文化的公共场所发生作用,因为那才是这些问题原本生根的地方。人们会以为在这种媒介中有机会出现组织社会的新方式。当然,这样的想法常常来拉拢我们,而这是我刚成为艺术总监时反对的倾向之一。我的确认为,那时的艺术节某种程度上正朝着过于自由放任的方向移动,例如抵制创意产业,非常幼稚地赞颂开放性。今时今日,我认为它那时面向了更加广泛的人群,到我加入时,它已经引起了媒体艺术社群之外大量公众的兴趣。
是啊,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儿童托管和面向孩子的项目形式。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作为艺术节来说,即使我们通常不具备如此资源,但仍应该考虑。
回想2012年你就任艺术总监时,正值一个至关紧要的时间点,存在于两段迥异但并非互斥的历史中:2008年金融危机浮现出的现实主义,和通讯科技的主流化。到2012年,对金融危机的认知已经具体化—它并非一场偶发的黑天鹅事件,而是一个硬编码分叉(hard-coded fork)永久地生成了一条未来的新轨迹。2012年也见证了移动设备科技被广泛采用的重要一步:Facebook上市并收购了Instagram。
在此背景下,你策划了任内第一届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主题为"不/兼容",将不兼容视作文化生产的基本原则。艺术节持续处理当下的问题,并同时展望不确定的未来。周遭环境每一年都更加速变化,你如何面对当下?举例来说,关于人工智能的主流新闻话语放到五年前必然不会是主流。数码文化被广泛接受,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让你开展工作更加困难?
事情会循环上演,不仅仅是这些作为流行词汇的话题,还有全球以不同方式展开并重复自身的事件。2008年以来我们也经历过其它的金融崩盘,导致了其它的社会回应,我认为这是不得不以历史意识应对。这始终是我的方式之一—尝试同时向后和向前看,这是为了应对当下,避免怀旧或未来主义。我有媒体考古学的经验,这也一直是我的方法之一。
我很奇怪这些事情被作为新的转变而受到争论,从我自身看来,这一转变从控制论(cybernetics)兴起伊始已经持续了30余年。对我而言,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的文化功能是保持这一批判反思的功能,这至关重要。不是说它变得不再切题了,可能恰恰相反,因为这些议题现在被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上探讨。
艺术节因此更加切题了。
正是如此,这也将我们置于更具挑战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在过去两年已经注意到,仍有许多需求等着我们实现,要提供答案、保持平易近人,并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德国的高雅文化艺术节的优势地位来应对这些议题。见证各个派系集团对我们项目的各部分作出的不同回应是很有趣的。我对用亮眼的装置讨好媒体艺术受众没有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亮眼的东西。我不是完全站在对立面,只是觉得人的注意力应该被正确的东西吸引。
我们不应礼赞最新潮的媒体艺术装置,而应该把鲜为人知的讲者请进会堂,应该开展一些疯狂的项目,比如2013年的装置项目气流管道式的物流输送分配系统"OCTO-P7C-1"。我认为不管是资金上还是受众上,我们的现状是奢侈的,能让我们做上述事情,而不是抛出一些简单的作品。我真的希望艺术节将来会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发现新的方法来应对新的政治利益与希望在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上寻找答案的观众。
说到不再设"核心"展览,这一决策是否因为你注意到若要捕捉和管理"感受的结构化",使得传统展览的单一舞台形式不再可行?是否可以这样说—传统展览模式不过是另一种中心化模式,它贩卖甚至牺牲集体主体性,换来个人主义?
对展览的需求,显然可归于一种非常西方、殖民和表现化的逻辑,我认为有必要怀疑并远离这种逻辑。我不是反对展览本身,我自己也喜欢看展览,但将文化打包塞进这种格式里的持续需求是有些可怕的。尤其是在一些语境中,比如艺术节—它的传统是要做出聚焦国际的呈现—还有各种奖项等等,这种需求已经过时了。紧随这种范式之后而来的是双年展文化,我认为我所带领的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是慢慢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论好坏。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我刚上任时的想法是,将这个由"创意人群"构成,并因看似没有什么重点而消散的艺术节,用策展的形式聚合起来,所以那时我引入了更多的展览。
说到策展主题为世界的失序带来秩序并引发批判思考,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加谦逊的方式,这就与你所说的有很大联系—依赖于反学习(或至少是某种谦虚的学习)过程的革命性主题的出现。我在之前的几届艺术节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
我们已经给予这些社交和推广的量化模型太多的信心,并行的是某种后表象式的策略。我认为当下离开Facebook是正当合理的,回到几年前这一举动可能会给我们招致麻烦,甚至包括资金方面。我想人们明白这现在成了问题,也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公立机构这样做是负责任的。我自己从没用过Facebook,我知道这有些傲慢,但到如今,很显然上Facebook变得并无必要。我认为应该有替代选项,或许这将激发我们去建立这些新的选项。
是的,这一决定不是要说社交媒体沟通本真是不好的。我们毕竟还是具有情感主题与感觉结构。2020年2月2日,我们举办了一场沙卡·麦格罗顿(Shaka McGlotten,译注:Purchase College-SUNY媒体研究和人类学教授)主讲的演说,探讨爱与社交媒体。麦格罗顿以酷儿的视角扭转了我们对寻常之物的看法。
我知道"建造"(engineering)是个很重的词,但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建造健康的文化,因为线上用户不必与这种事情打交道。社交媒体在损害创意产业内部,因为人们屈从于数字游戏,有多少关注和赞,而这恰恰代表了政治最糟糕的一面。
今日如果你是创作者,就必须在社交媒体上露脸。这是一个例子。它存在于每个行业中。
《The Nth Degree》首先是一部非常直白地探讨阶级的电影,这种方式在许多新媒体艺术里常常被忽视,而其视觉语言放在BBC Channel 4播放也不会违和。作品呈现出显著的工人阶级语调,几乎是肯·洛奇式的(译注:肯·洛奇为英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导演,把社会主义者的信仰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你能否展开谈谈将这件作品纳入艺术节的决定?
这一决定主要来自我们的策展人Florian Wüst,但我们一起组织了研究小组"不安的联盟"(Uneasy Alliances),其中我们试图解决的议题之一便是这个集体主义新形式的问题,还有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议题。我们也试图联结起一些批判科技的行动主义者与致力于反对士绅化的人士,以此观察联盟的建立是否可行并足以抵抗"柏林作为创意之城"的发展—你知道的,这样的创业文化从政治角度看对城市有益,会带来更多的艺文活动,但事实上它引发的是更加不确定的工作条件和风险资本(译注:为投机性商业投资提供的资金),这必然导致房地产的价格水涨船高。
在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我总是想要强调横截性(transversatility)而非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y)。艺术节一直致力于谈论当下全球正在发生之事,而纪录片则作为影像来说有着强烈的历史意义,所以将这部影片囊括进来并不矛盾,我们以前也展示过类似的作品。这件作品是有些不够典型,但如果你细细观察我们的计划,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结。例如罗里·皮尔格林(Rory Pilgrim)的作品指涉了科技,但它也呈现出相似的工作进程,将人们带入一个集体性过程中,而这后来也成为了皮尔格林了不起的表演作品《Software Garden》的一部分。《The Nth Degree》也与Robin Vanbesien关于雅典的团结运动的电影《Under These Words(Solidarity Athens 2016)》(2017)相互关联,后者更多的是应对希腊的社会气候。
我们这些年来持续在做这件事。同时表现出来的是,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不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场所。为了接触科技领域的人士,我们仍然保持与影像文化和媒介理论的联系。我认为有必要找到间隙中的空间,因为这些边界已经以机构为基础被建立起来。但如果想要通过我们雄心勃勃抛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就不能去迎合什么新的媒体策展人,告诉我们"哦这个在我这儿行不通"。那不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抱着乌托邦式的理想,认为这些展览能产生影响力,引发改变,即便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它们也在社会中具有续航力。
你能谈谈在兴趣上的转变吗—关注的不仅是集体化,还是集体福祉?你认为过去一年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的角色发生了切换吗?
这是以一种开阔的表现方式,表达朝向某个并不幼稚的目标的愿望—这目标不是硅谷风格的"我们在拯救未来"。2020年transmediale跨媒体艺术节的方法之一就是以更加积极肯定的方式,和你所说的共享生命体验相关联,并且将我们已有的东西作为起点,尝试寻找可以建立在此之上的品质。不是只有一个"我们",在集体主义中有多个"我们"。甚至"我们"的代词也有待商榷。存在一个因新主体性和新集体主义的萌生而颤栗的艺术节,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需要在不预设判断的情况下前进,它不是要反驳消极性,或是反驳随着自我优化带来所谓的主观恐惧。它也拒绝假设我们具有批判的能力。—[O]
翻译:钟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