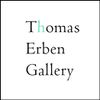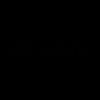以逃逸作为在场:阿彼察邦“狂中之静”的意识机制与边界破口

展览现场:"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狂中之静",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3月15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台北市立美术馆。
梳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创作脉络过程,会察觉阿彼察邦并非使用线性与直面的方式,而是以逃"离"作为一种逃"往", 透过"反向的逃逸状态"来指涉对象物的存在/缺席,以"逃逸"作为"在场",以"缺席"作为"存在"。
此次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的个展"狂中之静"(展期: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3月15日),源于阿彼察邦回顾展览计划,此前相继于2016年清迈MAIIAM当代艺术馆、香港Para Site、马尼拉MCAD与芝加哥SAIC等机构展出。走进展场中,整个展览化身为一座巨大的造梦机器,透过光影交织作用,观者仿若置身于阿彼察邦制造的幻梦中,而梦里看见的是阿彼察邦的同事、友人、伴侣、家与不特定影射的政治社会局势,从第一部实验影片《子弹》(1994)到在南美洲拍摄"备忘"项目的部分作品《备忘:海边的男孩》(#Memoria, Boy at Sea,2017),媒材形式包括短片、录像、摄影输出、部分手稿及档案素材等,使观者透过此座造梦机器得以窥见阿彼察邦有别于长片的创作面向。
梦与睡眠成为阿彼察邦创作中既轻且重的元素,无论是此次未能展出的长片《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2010)、"狂中之静"展览中纪录亲密伴侣睡眠的三频道影像《提牧》(2007),或是《俳句》(2009)中阿彼察邦记录下《极乐森林》(2002)的拍摄现场,一群青少年被催眠机后睡在时光机的那幕,与梦相生相息的睡眠在阿彼察邦的创作中,作为在泰国军人专制政权与纷扰局势下的一种"逃离",因为在睡觉的情境下可以摆脱控制,在无意识中连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让渡控制的身体主权,方能成为一种真正自由的无声抵抗。
《虚构》(2018)描绘着在夜晚时分,扰人的虫子因为趋光而飞舞在象征家的日光灯管周围,阿彼察邦环绕于此,试图于日记本上记下一个梦。展场使用玻璃投影,使影像的透明感消解实境,玻璃也使得影像伴随著光映射于地面,也因此观众得以站在玻璃投影折射于地上的字境之中,如同艺术家将日记写在观者的身上,使实际的光与内在的光的互动过程对身体产生转变,就像把意识层面往身体输送,光影让人无法觉知现实,而是自己将自身带入幻境式的真实。此刻身体并不真的去感受什么,而是使觉知跟幻觉交缠,而现实跟梦境也于此模糊了边界。
梦中梦里关于家的存在,成为泰国政治局势的意识缩影,《灰烬》(2012)中的一段自白[1]得以清楚道尽阿彼察邦对于家的感受,处于敬爱与恐惧、逃离与想望两者之间的介质与矛盾装态,透过梦中梦指涉家乡缺席的存在。亚洲家庭因为经济因素的关系,家中多装有白光灯管,在《纳布亚魅影》(2009)片头的日光灯所散发冷冽的白光象征阿彼察邦对家的记忆与温度感知,在一座有着共产幽魂与历史伤痛的小镇纳布亚,发现一群不应该独留的年轻人踢着燃火的足球,在黑夜与火光魅影中的嬉闹,最后燃烧投影布幕,烧尽后残余投影机的白光回应着片头日光灯对于家所隐含的趋向性与破坏性。
此外,展场中架设了许多微型投影机,投射着许多阿彼察邦的影像日记,梦境的片段、家乡的雨季与正在医院进行疗程的父亲,非高清的画质更能带出一种像似在梦里斑驳模糊的手稿感,使观众感受阿彼察邦如梦似幻的影像书写日记。
出身于泰国东北部的阿彼察邦,紧邻边界的生活态样时常成为镜头下的素材,《烟火(档案)》(2014)刻画坐落于泰挝边界上的小城—廊开(Nong Khai)城中萨拉鬼窟佛像公园中的动物雕塑,创办人Luang Pu Bunleua Sulilat根据幻想、政治神话、民间故事来打造雕像宣扬佛教教义,然而Luang Pu Bunleua Sulilat在其后被控为共产党员,被迫流亡老挝,并遭受政治迫害与不公对待,最后,这些公园雕像就像是在诉说著逃亡主人的抗争,阿彼察邦透过在黑夜中放烟火的光,一闪一烁地照映这些雕像,像似闪光灯拍下并投射出雕像背后的时代脉络与政治局势,让观者对瞬间出现的雕像产生凝视与肃穆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边界,还存在着一种社会身份意义上的边界。《无名的力量》(2007)纪录位于泰国东北一带的劳工,因应泰国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这些劳工随着资本的需求而辗转在不同场域中移动。移动的泰国劳工变相成为泰国景观的一环,货卡上的劳工或是兴奋地舞动着身躯,或是开心地不停诉说着却被消音,在资本建立的幻梦中讽刺劳动阶级的边缘化与失语,阿彼察邦将自身投射在劳工身上,同时也被泰国这股政治与宗教的诡谲混合体驱动着。
另一种边界是关于神灵与魅影的边界,背后所牵涉的是国家认同与信仰的关系。泰国的三色国旗,承载的是国家民族对泰国的认知—红色代表土地、人民,白色代表佛教,蓝色代表王室。泰国的发展与王室、军政府、佛教脉息相生,因此,谈到泰国,就很难将信仰独立出来讨论。
阿彼察邦曾经提及鬼魂之说不是不存在,而是如同记忆,作为对自身的一种投射,如同长片《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2010)中妻子回来的情节,关于神灵与魂魄,艺术家认为泰国对于神灵的崇拜跟信仰其实隐含著恐惧与控制,热衷的反面其实是让渡自身的主权,使自身被控制。
象征王室的录像作品《宫殿》(2007)将展间映染成火红色,此中数个角落中闪烁着去除边框的动物影像,仿佛游走于展场中的魂魄,影射着一种泰国性—象征着遗产与崇高的形象根植于泰国血液中,宗教与政治对于思想的双重钳制形塑泰国的主体身份认同。泰国并不是被他者殖民,而是被自我殖民,从内部产生的潜殖力量相对隐性且固着。
阿彼察邦以缓和且迂回的诉说方式,透过睡眠、梦、隐晦的场景、碎片的记忆、神灵信仰与鬼魅、边界的模糊性而投射状态与叙事的不可见,不直接指涉,但却一直存在自际产生的一处破口。在破口处,因为缺席且此状态越发持存著,在此阿彼察邦指涉的并非某种政治状态与社会背景,而是透过梦的意识机制,追寻自身与被指涉的对象物(政治、社会、经济、家乡等)的关系。这关系持续存在却无法被概括并捕捉全貌,并且持续变动着,既如梦般轻又如魇般重,成为一种"沉重的飘浮"。结合展览空间的对话关系,转化成为沉浸式的身体觉知,建构起专属于阿彼察邦特有的意识机制。
在这座"狂中之静"造梦机器中,观者如同置身于阿彼察邦式的幻影与梦境中,对比于外在现实世界的狂乱,伫立在这个梦里,有着属于阿彼察邦特有的静谧氛围,如同沉重地飘浮在一场自我觉知的梦里。外面局势纷扰,梦里岁月静好,但这个关于阿彼察邦的梦仍然镜射因缺席而不可见的关系,持续地推移着一切的未知沉潜的量能。—[O]
[1] "我发现那是梦,一个梦中梦,我拿了一支2B铅笔,在纸上画了图,那是我回到梦中的路,我不断回头看着......,那些巨大的画面,试着复制它们,模拟那些色彩,结果画出来的竟是我的家乡,是一栋建筑?是几间我记忆中的建筑,在我的记忆中,那些都是房屋,那是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小镇,我拼命画,拼命回想,深怕这飘渺的梦会消失,后来这色彩渐渐变淡,梦变成了黑白色,我好难过,努力想记起它的颜色,这时我才知道做的梦是彩色的,我画的是我的家乡孔敬。"阿彼察邦・韦拉斯塔古,《灰烬》,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