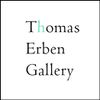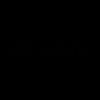陶亚伦的幽灵复茧:虚拟真实的增生与织覆运动

陶亚伦,"徘徊的幽灵"系列作品,2020。展览现场:"无处不在的幽灵",台北当代艺术馆,台北(2020年08月22日至2020年11月1日)。图片提供:台北当代艺术馆。
早在1932年,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推出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便首先提出虚拟实境的原型投射,"头戴式设备可以为观众提供图像、气味、声音等一系列的感官体验,以便让观众能够更加沉浸在电影的世界中。"某种程度 赛博朋克运动之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于其著作《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中提到"未来已经在这里,只是尚未普及。"的说法似乎回应了此种想像的可能性。
在2020年的当下,穿越时空触及艺术、科技与感知的变异,关于虚拟真实,我们能确认的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在艺术家陶亚伦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个展"无处不在的幽灵"(展期:2020年08月22日至2020年11月1日)中,不被确认,乃是悬置。
从台北当代馆一楼至二楼,得以窥见陶亚伦的创作脉络,他将整个美术馆视为一个作品,或者可以说他将整个美术馆打造成一个造梦机器,从一楼入口处动力装置《梦》(2015)就仿佛在预告观者进入艺术家创建的造梦机器中,透过巨大透镜折射至投影布幕的成像,诉说着我们肉眼所见的真实并非真实,抑或我们投射的虚拟方为真实的提问。
第一个展间的光影装置《自我的显像仪》(2013)与《灵"光"乍现》(2013)利用菲涅尔透镜聚光呈相的特性,使人得进入一定距离方能折射成相,探讨自我主体与外在环境、显相与幻相、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下一个展间中的《留白》(2012)则透过在实体空间打造虚白圆弧无死角的空间,结合光影变化,抹除人类视觉惯常透过x轴与y轴定位空间的本能,让人无法锚定座标,让身体进入一个虚拟却又真实的空间体验。
在一楼靠后展间中的作品《幻灭 No.1-No.6》(2020)将AR扩增实境结合当代馆馆舍空间,撑开废墟的崩坏空间,再一次透过视觉的感知叩问"现实"与"真实"的差异性,会不会人类肉眼所见的现实不是真实?不同物种所见的现实是否能够切片出真实的样貌?而真实究竟为何?抑或人类所追求的真实是否不存在于一个对象物或者地方,并且无法指涉无固着性、无固定形象,而是存在于不断变化的追求之中。
在一楼至二楼的楼梯间投影着一个巨大的虚拟实境启动键,走过一又二分之一的楼梯回廊,我们在真实与虚拟之际转换,也象征着按下了启动键,正式走进虚拟真实的造梦机器,开始体验《徘徊的幽灵No.1》(2020)至《徘徊的幽灵No.10》(2020)共十件虚拟实境作品。
因循载人的动力装置与头戴式设备中虚拟实境的影像内容,作品可分为垂直上下与水平位移的观看方式。其中《徘徊的幽灵No.2》(2020)和《徘徊的幽灵No.5》(2020)使身体感知产生垂直位移的观看经验,前者引领观众从空中下移至地窖,视角从俯视一个巨大人物坐像的头顶逐渐下移至坐像脚边形成仰角,透过近身的凝视召唤着伟人与救世主的英灵,象征着威权专制的权力不对等;后者缓慢上移至红色天幕中,中央的巨型雷达象征着国家资本的运行与监控,形成一种中心与边陲的对抗关系。
《徘徊的幽灵No.1》(2020)、《徘徊的幽灵No.6》(2020)与《徘徊的幽灵No.10》(2020)是以水平位移的动力机械载人进入虚拟真实中,其中《徘徊的幽灵No.1》载人滑移至一个监狱中,高塔象征网路数据化身为权力中心,观者无论移动到哪,都会被高塔上的探照灯紧紧跟随,持续探照且监视着自己,如同福柯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 )中无处不在的监视与规训的权力关系。
《徘徊的幽灵No.9》(2020)则是使人进入第三国际纪念碑——由未来主义艺术家塔特林发起的计划——透过一个想像的高塔,塔尖将各种决策投射至云层上,隐喻着以共产主义与人民权力作为运作模式的国家机器。
这十件虚拟实境的作品,从内容上分别指涉数位威权、资讯监控、政治极权、资本宰制、网路殖民化、军国主义、反思战争等,如此不在场的在场,如同现今社会下无处不在的幽灵,存在于不存在之间,在真实与虚拟过渡之际生成,幽灵作为一种虚拟的实存,或是作为潜在的来临者的虚拟真实、或是电子游离化的虚拟身体、或是意识形态的阴魂不散、或是无所不在的治理技术。
此外,这十件虚拟实境作品的观展路线,皆从虚拟的当代馆展间启程,也回到当代馆的展间,展延十个虚拟的当代馆空间,扩延台北当代馆的展览空间,形成了真实与虚拟的空间连动:美术馆的现实空间、VR的虚拟空间、观者的感知空间。在进入现实与虚拟的空间之际,撑开另一个感知的空间维度,让幽灵得已回荡其中。陶亚伦利用动力装置与虚拟影像的结合使观者得以体验产生时空的差异性,而在启动体验的那刻,时间仿佛被延迟,空间被扩大,产生一种时间的内爆与空间的外延——观者的身体水平移动距离不长,但意识却感觉在作品的虚拟空间移动了相当长的距离,或是现实空间的身体静止不动,但虚拟身体已经垂直移动了几层楼的高度。
这样下移与上升的感觉,透过虚拟身体触发着真实身体的神经细胞,在空间扩延与时间迟延的多层次与交互作用下,串连着虚拟身体与真实身体的感知细胞触发过程,像是进入了层层的梦境,梦里又再进入着第二层梦,然后再进入着第三、四、五......层梦等,最后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拟模糊了交界,促逼着人类感知的时空复层。
同时,在作品中,无论是身体的水平或是垂直移动,视角与位移的方式皆受控制与设计,形成一种被动的凝视,于是,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造梦"机器为人造的梦是个恶梦。
不同于其他艺术家善用虚拟实境的主动性,艺术家将恶梦作为他创作虚拟真实的参照,采用捆绑现实与虚拟身体产生的被动式凝视状态,使观者进入他的作品时,就如同进入人类做恶梦的拟态,身体因着动力装置无法动弹,形成一种身体在现场,而意识是封闭的状态,所有作品都是无声的,使观者能够因着现场环境音而清楚意识到自身的在场,不停地在虚拟与真实之际游移,仿若做着恶梦般的体验感,实践恶梦即是最具威力的影像感知能动性。
真实产生在真实与虚拟串连纠缠之际,且在进入的那刻自我生成,于此,被动地凝视主动地解放了人类的感知能力。
达米安·布罗德里克(Damien Broderick)曾在其小说《犹太曼陀罗》[1](The Judas Mandala,1982) 提及"基本上,虚拟实境是我们自愿创造一个包裹我们的'茧',而且它还会同步修改我们所处的环境。"——在虚拟实境的"茧",指涉着两个方向的运动过程:"皮茧"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不断"增生运动"与"丝茧"织构包覆所产生的"织覆运动"。
一个方向透过科技发展与演算,拓增虚拟实境的效能,使感知能够进行皮茧的增生运动,另一个方向则作为丝茧呼出的缠丝,轻透柔隐,以一种不规则且多层次的方式编筑,且从未有重复的路径。蚕吐丝作茧是为了包覆,但在此所指涉的是一种意识与感知的编织包覆运动,使物理的现实往内穿透,丝茧的不规则的复数路径亦乘载时空的向外扩延。
精准地说,虚拟实境,这样人造的"茧",是人透过对感知与意识进行"增生"与"织覆"运动而持续串连反馈人类对于感知的时空机制。
最后,结束展览的观看,就如陶亚伦虚拟实境作品中,开始的空间也是结束的空间。展场入口墙上的大字,"潜在的来临,悬置了一切的在场"( The potential arrival leaves every presence hanging.),暗示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于《非人:漫谈时间》(L' 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一书中谈及思想如何摆脱身体时,言及"精神不是被领导,而是被悬置,我们并不给它立什么规则,而是教它去迎接,我们并不是为了建设什么而清理出更空旷的场地,而是排出一个空地,快要被给予的、半明半暗的事物可以进入空地而且这个空地将改变事物的轮廓"。
就在潜在的将临如快要被给予的、半明半暗的事物进入此无法具体指涉的感知维度中,促逼着幽灵的将临,幽灵被悬置在一切在场于不在场之间、存在于不存在之际,在空气中回荡着,让想像的对象成为将临且尚未想像的东西发生的起因,跨身为一种"悬想"。
为了迎接尚未被思想之物的到临,幽灵于未来的"尚未来临"与过去的"已然不再"之际现身,开启更多的可能与未知,使人回归艺术的本质,就如陶亚伦认为艺术的政治性不在讨论社会议题或是产生效应,而是艺术自身就有着结构与再解构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使人因而再次提问:我们眼前的真实是否真实?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还是我们所投射出来的存在?—[O]
[1] 讲述一个失业的女诗人被抛向了四千年后的世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