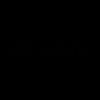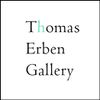达伦·贝德、李明及策展人孙熳的一次纸上“巧遇”
展览现场:'跨服聊天',天目里美术馆,杭州(2023年4月29日至9月3日)。图片提供:天目里美术馆。摄影:Wen Studio。

展览现场:'跨服聊天',天目里美术馆,杭州(2023年4月29日至9月3日)。图片提供:天目里美术馆。摄影:Wen Studio。
相遇可能不会发生,正如它可能发生一样。没有决定性因素,也没有决策性原则事先决定着这种非此即彼——这就像掷骰子一样。'骰子一掷,取消不了偶然。'一次成功的相遇,无法确保它的持续。正如它可能本不会发生,它可能再也不会发生:'运气来去变幻自如'。[1]
天目里美术馆一楼的偌大展厅被改装成了两个大男孩的 401 号公寓。达伦·贝德(Darren Bader)的旧作《沙发;假沙发》指定了两组现成沙发家具作为他的艺术创作,将展览"跨服聊天"(2023 年 4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的开端改造成了客厅,并邀请观众坐下观看沙发前电视中播放的节目——李明的"烟士披里纯"(2017,2018)。如此参差对照的组合方式,也为后续二者作品的布局拉开序幕。在进入明亮开阔的展厅前,首先有由帐篷打造的"兔子洞"。观众弯腰俯身便顺势坠入一个尺度骤变的空间。迎面而来的高挑空间与开放格局,顿时让身体失去对日常的丈量,从而向两位艺术家经营布置的荒诞敞开。
展览空间几乎没有搭建隔墙。策展团队通过改变作品的输出形式实现简单的区域划分。如在工作室区域,李明的影像作品《运动》(2014)借八个电视机的横向串联充当了"矮墙";达伦的《开启新文明的 109 个物件》则成了工作室的物料台占据了一大块地面。在"餐厅"中,达伦的《水果,蔬菜;水果和蔬菜沙拉》将果蔬视为"大自然的完美雕塑"进行展示与料理,并为观众提供餐食服务;而李明的《屏幕幽魂》(2016)中那些由油画布制作的大型风筝,将印记不明的苹果手机贴膜呈现为3米高的黑影悬浮于上空。在卧室区域,达伦的《诗(领标)》邀请观众翻看衣架上服装的标签;李明的《寻梦启示》(2017)与《寻梦启事》(2017)则让衣柜成了一个既是载梦匣又是寻梦舱的方体。
对话展的形式通过模糊两位艺术家的创作边界,得到了他们都未曾被勾勒的轮廓。不可否认,这样的做法常常伴随着危险,因为艺术家赖以为生的品质正是创作语言的独特性。机构主义时常要求他们在保持这种独特性的同时,为作品流通提供一套简明扼要的话语。这让群展或策展性展览大多呈现为一场权力斗争。如同黑格尔笔下展开殊死搏斗的诸自我意识与他者意识,展览最终是属于获胜者的——他要么是在群展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个体,要么是信奉强策展方法论的策展人。而天目里的展览却为我们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景象。我几乎看到了一种女性主义式策展学的包容与慷慨——诸个体在其中通过他人成为自我。
因此,我希望借三次相互平行的采访,让策展人孙熳与两位艺术家分别凭自身印象回溯这段绵延三年的特殊展览经历,请他们谈谈展览的契机、中间的变化与各自的感受。尤为有趣的是,两位艺术家不约而同地提及天目里策展团队在此次合作中显示出的特殊性。这当然与策展团队所相信的方法论有关:一种体现照护与关怀的关系性实践。
孙熳:这次展览的沟通过程很长。这个展览计划在疫情前,当时场馆甚至还在筹备期间,就定下来了。最初的构想是做一个中外两位艺术家的对话展。原本都是些很初步与模糊的想法。**疫情前,我们面对的世界仍是地球村的状态。因此,最初对伦敦地铁播报音"小心间隙"(mind the gap)的引用,是希望积极回应不同文化、不同个体之间的差距。但疫情改变了这样的情况,间隙变成了一种近乎隔绝的"隔阂"。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说法,是为了抱有某种期望,是希望在意识到这个隔阂的情况下,仍能乐观前行。**起初为了绕开语言壁垒,我们提议让艺术家以作品接力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是一个三方熟悉彼此的过程,策展团队也开始逐渐了解他们的思维方法。这个对话因为疫情出现过中断。后来开馆的日程终于确定,我们又开始回顾之前的沟通,对艺术家的作品做全面研究。因为他们彼此没有见过面,达伦也没看过场地,策展团队需要尽力沟通,让他了解场馆发生的事。与此同时,我们对作品进行梳理,逐步讨论出作品清单。在我看来,两个艺术家的作品形态有着不同的空间向度,李明因为影像偏多有纵深感(Y轴),达伦的作品则更适合水平铺展(X轴)。为了平衡二者,我们在这基础上调整观展节奏并划分空间。帐篷作为兔子洞的布置指涉了爱丽斯漫游仙境的情节,也呼应了两个艺术家的作品气质。因为他们都敏感于生活的庸常,我们最终决定将展陈设计为一个房间。
展览始终处于一种生成状态,因为一直有新点子涌现,展览的文字是最后才被总结出来的。我们将展览的中文名定为"跨服聊天",是希望不管聊天有没有效,也能让观众加入这些对话。作为对话展,这个展览有着许多沟通、让步和妥协的成分。而作为策展人,我认为英文的"策展人"(curator)并不是中文语义中指代的"策展",而是照顾与关怀(cura)。因此我在展览实现的过程中,试图以最大程度的共情了解工作伙伴,熟悉他们的为人以及偏好的合作方式。策展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概念先行的事,而是让一切最终汇总在一起。
达伦·贝德:我们应该是在2021年的夏天开始建立联系。我当时还带着两个月大的小孩,经常一边带着他遛街,一边回微信。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副馆长吴天鼓励我们通过作品对话。然后李明就发作品给我,我则试图去理解它们。我们偶尔会对发出的东西做相应解释,因为有些作品需要一些语境和话语的补足才能理解。展览的名字"Mind the Gap"不仅有趣还言简意赅。因为它的确是关于两个从迥异文化背景出来的人如何相遇的故事。虽然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但在感性方面,我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映照着对方。我们通过作品了解彼此,即使它们很多时候需要相应语言环境的理解力。这个过程被她们形容为"打乒乓",作品来去的节奏的确很像这个运动。后来有段时间,我和李明都有点钻进区块链和NFT的领域,好奇它们的可能性。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它的经济效应,而是诸如新技术分享的审美信息这类更复杂的议题。但后来因为疫情,这些讨论被搁置了。直到2022年6月,我们才试图重拾这些对话。我们通常会在网上见面,孙熳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李明看起来很有趣也有着某种神秘感。但我太忙了,因为那时我需要带娃,纽约的生活并不容易。后来我和李明的交流变少了,因为我需要解决运输和海关的问题。但孙熳觉得,正是因为在这么多变化进行的情况下,我和李明的沟通还应该继续。后来他会发英文消息给我。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翻译软件,还是有什么人坐在他旁边给他翻译,但他的英文突飞猛进。他似乎有某种魔法,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精通英文的人。我觉得他可能真得是魔法师。我不认为我是,但他或许真是。后来我们在展陈的合作上也达成共识。但我的第二个小孩又出生了,所以我最后没能去杭州。
我们尝试了五种不同的沟通方式,从一开始微信沟通,到腾讯会议,后来更多地通过Instagram和邮件,我也在线下见了馆长弗朗西斯科·博纳米(Francesco Bonami)。展览设计师郭家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展示了十分直观的展陈设计,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魔法。我当时就确信展览效果会非常棒,因此几乎没对提什么修改意见。我很高兴看到孙熳的作品选件——显然她也和李明进行了紧密合作。我和李明的作品显然在视觉层面产生了化学反应,虽然我不确定这种反应是否也同样作用于语言层面,但我们似乎都对一种难以命名的游戏情有独钟。我通常会深入参与布展并工作到最后一刻,但在这个展览里,我既没有设计展览,也没有参与布展。我第一次把展览事务转交给布展团队,让她们为我转译。策展团队的理解力与效率让我感到安心,这种情况实属少见。它也偶然呼应了"Mind the Gap"的意义。
李明: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工作方式——和一个在纽约成长的职业艺术家对话并实现一个展览。将我与达伦·贝德组合的提议来自吴天。我的英语很糟糕,贝德的中文水平比我的英语还差。但策展团队认为语言不通或许可以创造交流的新花样,她们提议:除非有极个别特殊的情况,我和达伦·贝德可以辅助翻译,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胡言乱语"(笑),这也是吴天对乒乓球游戏的提议并映射到作品中的由来。我们在微信群里借自动翻译功能,用作品"打乒乓"。根据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发送一件作品。我发出的第一件作品是《今天无事发生》(2012),达伦回应的则是《把助听器扔到火山里,你将得到一个走廊》。有时这种交流会出现误读,但也让人收获很多。孙熳全程都在观看这个游戏。然后她将我们交换的作品分类,总结出一些共性:动物(家禽)、文字游戏、音律韵脚、无意识的说话方式、价值转换、平庸日常。它们最终被组装进一个家的概念。我们之间的交流经历了几次平台转换,从微信、邮件到Instagram。我甚至提过在元宇宙碰面。跨平台的沟通很像穿越兔子洞。我们最终在展陈设计上把它转化为帐篷,让大家穿过这个空间进入开阔的展厅。
在这次合作中,主要与我共事的天目里美术馆此次展览项目成员几乎都是女孩,这对我而言也是首次。她们每个人都很智慧。从初期的雏形、中期的讨论(协商、想办法、加热或发电)、后期执行(提出建议并得到反馈),我一直都收获惊喜,并感到工作是幸福的。我在年初时做了一次塔罗牌预测,塔罗师告诉我上半年的状态会是"被动的主动"——"被动"是性格层面,"主动"是说在工作上会有很好的配合。我们有一个叫"mind the gap中分GAP"(非三七分的中分)的微信工作群。我在心里为群里的同事分别作了角色设定,比如:忍者(精通多项软件技能且有持续修炼的恒心,耐力超强且情绪恒定)、魔法师(在事情进入一筹莫展时刻能化险为夷,将事情扭转到新的出口,全程关照大家信心指数)、信使、山(永恒的有求必应);这里不做实名对应。相信她们更享受于隐藏在幕后,看着这一切顺利发生。
也基于上面的因素,我慢慢从眉头紧锁的自我控制欲到"放手"。像我这一类的创作者,总是习惯在推方案的同时,构想展示的效果。而且,自2015年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新倾向"个展之后,我比较明确地将影像和空间混在一起创作。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会从整体计算影像的屏幕尺寸、空间尺度、展示环境、行走路径、声音等等。但总体上,我都偏好幽静的、半昏暗的、包围性的,且音场完整的展示环境。但当我以俯身的视角想象天目里美术馆一楼的梯形展厅,站在梯形的尽头(长边的一端),望向另一头的短边:透视线的灭点、六米多的层高、精密的仿日光照明系统,这些都让我很难拒绝去尝试敞开边界的氛围。我也提前做过许多工作,看了贝德的大量作品和过往展览现场,以及信使给我发来的他本次的参展作品。因为他无法来到现场,并且认为我们比他更熟悉这里的情况,因此选择把布展工作全然交给团队。我在那个时刻也意识到,天目里美术馆一楼之前已经做了三季展览,团队的人从建馆初期就在,也没有人比她们更了解这个建筑。说到"家",那也算是她们"一半的家"了。既然如此,为何不试试?后来的情况就变成,我不断地在好奇、欣赏与学习团队的工作方式。我不控制什么,而是感到放松。人在放松时就能有觉察力。所以我慢慢喜欢上了配合工作,我也尽量做到有求必应。
"关系"是美妙的,它也可以被理解为"相关性",既辩证又具体。如果不参与其中,不在相关联之中,我们能说出什么所以然呢?食物可能无法说出自身的鲜美,但品尝者的味蕾可以体会,并用语言传达它的味道。而当我们都全力投身在这相关的网络之中时,所见即所得,我们又还能多说什么呢?在我看来,401号公寓不只是李明和达伦·贝德的家,我们要多多留心展厅最后一面致谢墙面上的所有信息。—[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