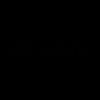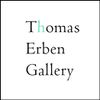用于“联结”的“帘幕”

展览现场:"帘幕",Para Site 艺术空间,香港(2021年5月15日至7月25日)。图片提供:Para Site 艺术空间。摄影:张才生。
"帘幕"(展期:2021年5月15日至7月25日)是香港 Para Site 艺术空间与上海外滩美术馆的第二次合作展览。此前第一个合作群展"百物曲"于 2019 年在 Para Site 艺术空间首展,而后以扩展版本巡展于上海外滩美术馆。
此次二回合作展"帘幕"强调表演的实践和戏剧的形式,可以视为对上海外滩美术馆的"百物曲"深思熟虑后的回应。如果说"百物曲"是舞台上各种各样的演员和奇观的热闹游行,那么"帘幕"揭示了造成表演可见的舞台和背景。
"帘幕"意味着"上演":拉开"帘幕",开始一场戏;关上"帘幕",就有了隐私。如果我们看到的"帘幕"和观众同样具生命力,该怎么办?无论字面上还是隐喻上,"帘幕"的多义性不仅仅是过渡对象、场景道具或修辞手段,而已是我们政治-文化-审美生活中活跃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展览中具有"主角"意义的作品是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1926-2017)的"历史照片"系列作品(1994-1998),该系列以超大尺幅的黑白摄影画面为特色。展出作品,如《历史照片:爬入——德奥合并,维也纳,1939年3月》 (1996/2021)记录了当犹太人被迫在维也纳安施卢斯(Anschluss)爬行和擦洗清洁城市街道时的状态,以及《历史照片:走入——圣殿山屠杀,耶路撒冷,1990年11月8日》(1996/2021)反映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发生的以巴冲突。

在 Para Site 艺术空间,这些平躺在地的图像上铺设了黄布,迫使观众主动掀起,探身进入布内才得见图像。织品的颜色——黄色——不仅让人想起犹太人在过去历史中被迫在其右手佩戴的黄色犹太星标记,在此地,这是 2013 年和 2019 年运动的标志性颜色。
沉重的织品,使得探身入内变得困难。观者不能只是抬起一角随意窥视,而只能爬进去,在织品底下勉强辨认出一些局部视觉印象,如人影、黑色皮革、白色水桶,人皱眉或搓手。帘布底下透漏着令人窒息的黄光。
在这个城市,将"黄"与"蓝"进行比较,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蓝"是支持政府和警察的派系象征色。这又带往了"帘幕"的另一层次,在展览中,不同色度的蓝色形成一首忧郁的挽歌,讲述了其他时空中的创伤和悲剧。在这里,蓝色与黄色有可能结成联盟。
在Soho House的延伸展览空间中,一溜透明的蓝色窗帘挂在窗户上。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在艾滋病成为社会现象期间创作的《无题(情人)》(Untitled [Loverboy] ,1989)——当时美国的许多男同性恋者正在死去,而此作品中的"情人"正是艺术家的爱人罗斯·莱科克(Ross Laycock),他在作品面世两年后去世。
然而,现场的蓝色窗帘却充满活力——它随着现场的气流中摆动,无论是通过空调还是因观众的接近。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这位艺术家的情人在临终前,呼吸节奏加快,瘦弱胸膛艰难地起伏,直到停止,静止不动。命运为他的生命拉上了"帘幕"。
另一件蓝色作品是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 的《蓝》 (1993),是艺术家在因艾滋病致盲和死前创作的最后一件作品。作品中,伊夫·克莱因(Yves-Klein)的蓝幕在影片中占主导地位,嘈杂的声音与器乐和歌声交织在一起。这些声音,包括贾曼自己讲述了从同性恋者的生活经历、艾滋病毒抗病毒治疗、诗意的蓝色沉思、幻觉和遐想,以及过去的情人和死去的朋友名单。
关于死亡和分离的意象,在展览中比比皆是,这样的主题也与当地人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许多人因害怕压迫升级而选择离开这座城市。韩国艺术家林珉旭(Minouk Lim)透过《安蒂冈妮》(Antigone,2015)——引用古希腊知名悲剧《安提戈涅》,使用常见的拍摄设备和废弃停产的材料所组成的雕像——警世性地劝告在地人尊重家人就要冒着叛国与死亡的风险。
类似的提请,也可在周涛的《蓝与红》(2014)看到。在这段不到半小时的视频中,展示了艺术家于 2014 年在曼谷居住期间所拍摄的景象。当时这座城市正处于政变遗续之中。
艺术家将这样的视觉材料和家乡广州平凡的城市生活图像无缝交织,创造出基于纪实的虚构叙事——当家庭聚集在公共广场时,巨大的 LED 屏幕照亮了一座蓝色的夜城。军用帐篷整齐地排成一排,远处传来枪声。摒弃视觉材料的地理特征,周涛似乎在日常生活的裂缝中看到了运动、抵抗以及团结的可能性。
"帘幕"的意义,在 Xyza Cruz Bacani 与李爽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内部视角。拥有在外籍家庭帮佣10年工作经验的 Xyza Cruz Bacani,成为倡导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通常是女性)家庭佣工在香港以及全球其他移民社区的经历的代言人,其纪实性镜头亦瞄准这些人群。
在《中环人行隧道,香港》(2019)中,艺术家捕捉了这些佣工在周日(他们唯一的休息日)在城市的街道上使用纸板、各种织品和屏幕将公共空间切割出一个临时空间用来聚会、娱乐和休息的状态。同时,艺术家指定使用普通塑胶片装裱作品,使得观者的形象会因为反光而叠加在影像上,造成一种"帘幕"前后的视觉景观。同时,形成"隔离"的塑胶片,也让人想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当下,不断增加的公共屏障和口罩所生成的免疫与安全幻觉。
揭露女性劳动力的真实境况,并不止步于外佣。生活于柏林的李爽,邀请她的朋友在一个悬吊的摄像机下,对着催眠式的画外音表演出诱人的姿势的录像作品《AETHER》(2021)。
在"帘幕"现场,被投射到天花板上。坐在豆袋上的观众,如同作品里的女性,受到了来自于上的监视。在不断蔓生的监视制度下,我们都在为老大哥摆拍和对嘴。
远离这么强烈的公开曝光,"帘幕"在家族记忆场景里中得到疗愈。艺术家谭婧追溯了其祖父母在反共恐华情绪高涨的1950 年代,从泰国遣返回中国的过程。出于对祖父母自愿性的失语与迁移的创伤性健忘感到沮丧的她,以作品《阿雄出走了》(2021) 捕捉了已经过世的祖父化为一只狗,追寻其历史的过程。
展场中,艺术家创作了一排带有柠檬草气味的珠帘,让人想起过去在其祖父母在泰国的生活。展场地上杂乱的泥土脚印纵横交错。不见狗的身影,只见狗留下的痕迹,令人猜想狗/祖父已经踏上自己的旅行。
与之类似,犹太女性艺术家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 Ackerman)的录像装置作品《空冰箱里走在自己的鞋带旁(之二)》(2004)对大屠杀进行了救赎性解读。其中最感人的时刻,莫过于第三个视频中被投影到半透明的薄纱上的图像——艺术家的母亲、姐姐和自己,被同一创伤所束缚的三代边缘女性,分别在生命不同的时刻在日记上的笔迹。
最后,尽管"帘幕"象征性的策展框架略显松散,但却饱含诗意与跨域性——在不同的时空和个体挣扎之间,"帘幕"建立起跨时空的联结,为饱受创伤的"此地"提供了重要的批判和参照性。—[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