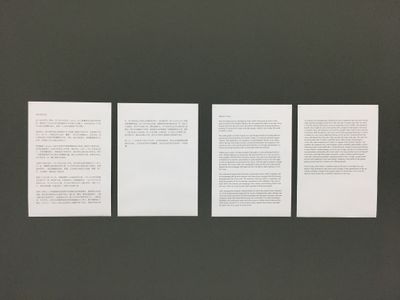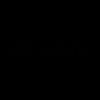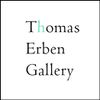关于“恶是”:疫情期间的策展笔记

蒲英玮,《世界主义指示牌(牧歌)》,2020。展览现场:"恶是",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20年4月11日至5月13日)。图片提供:蜂巢当代艺术中心。
2019年11月23日,剩余空间新空间首展"街角、广场与蒙太奇"(展期:2019年11月23日至2020年2月22日)开幕。此前因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影响,展览一推再推,直到2019年11月底才开幕。这个时候的武汉毫无疫情的征兆,所有的社交媒体尽皆沉浸在关于香港事件的激辩中。"街角、广场与蒙太奇"这个展览即是因应这一事件策划的。原计划2019年12月初配合此次展览举办一次关于"' 冷战前卫'与1960年代"的主题放映和论坛,因为考虑到展期较长,遂推到展览闭幕时举行......在这之后,我开始忙于2020年元月份的两个小展览。
2020年1月9日,收到蜂巢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杨鉴的信息,邀请我于2020年5月至6月之间,在他们的北京空间策划一个以80后艺术家为主体的绘画群展。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同时在准备给另一家画廊在北京新空间策划首展,档期计划也是5月份开幕(此展后来推迟到2020年底),时间上冲突不说,且由于都是群展,故决定再考虑考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折中方案。
2020年1月11日,在北京参加完王三庆先生个展"但在孤峰独往"(展期:2020年1月11日至3月29日)开幕后,当晚返回成都。一回来,便联系奕来画廊(Eli Klein),预订去纽约的行程。本来打算从武汉转机前往纽约,顺便利用半天的中转空档去剩余空间看看,结果因为春运将至,机票已经大涨,加之此前已确定参加1月20日下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PSA)的青策工作坊,所以临时改了行程,往返分别在香港和上海转机。1月14日上午,从成都出发先到了香港,记得当时的香港机场已经增加了关于武汉不明肺炎的申报和检疫程序,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和留意。当晚到达纽约时,肯尼迪机场没有任何相关的申报流程。在纽约的四天时间里,白天看展览,晚上看表演,丝毫感觉不到流感和疫情的迹象。展览开幕的当天(1月18日),寒风骤起,大雪纷飞,倒也应了展览的主题"不可抗力"(展期:2020年1月18日至3月18日)。可是谁会想到,真正致命的"不可抗力"其实已经悄然降临到了我们身边。
2020年1月20日中午抵达上海,此时已在朋友圈零星地看到一些武汉不明肺炎的消息,下午在PSA的青策工作坊讨论的时候,还特地提到了2019年年初郭瑛在大馆策划的展览"疫症都市:既远亦近"(展期:2019年1月26日至4月21日)。但想起此前朋友圈所传内蒙古鼠疫的消息,后来也不了了之,所以并没有将武汉新型肺炎当回事。当晚在虹桥机场路过前往武汉航班的登机口时,看到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中间有两三个人戴着口罩。孰料,几个小时后回到成都打开手机一看,朋友圈已经炸了,都在疯转钟南山宣布"武汉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的各种报道。那一刻,我突然后背一凉,庆幸自己没有从武汉转机,或许还真因此躲过了一劫。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和大多人一样,几乎是在恐慌、焦躁和心烦意乱中度过的。2020年春节期间,所有出行计划都取消了,只好待在家里,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浏览疫情变化。不过越往后,感受至深的不再是疫情,反而是社交媒体所传递的各种反常情绪和截然对立的激烈言论。后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令我们烦躁、困惑和忧惧的与其说是疫情和病毒,不如说是媒体和信息。
2020年2月10日,杨鉴发信息问我展览方案的进度,以及能不能将展览提前至三月底或四月初。也是在那一刻,我临时决定策划一个有关此次疫情的展览,虽然时间紧,但觉得也不是不可行。此时,一些国外的机构其实已经开始行动策划关于武汉疫情的展览,国内各大媒体、公众号也在编发各种相关的信息,每天朋友圈也看到艺术家们的响应和行动,捐赠、拍卖,还有主题创作,等等。经过简单的沟通,最初的绘画展计划临时调成不受媒介限制的大型主题群展。但我不想直接针对疫情做一个展览,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应疫情的艺术投机行为,我一向持持保留意见。但我也不想做一个无关现实或不痛不痒的展览,特别是在这种时刻,还是希望它能掷地有声,把疫情下的真实感受带出来,呈现一个有情绪的现场。
一如既往,我先确定了一个初步的方向,考虑到是画廊举办,我首先要做的是浏览本画廊官网,挑选可展的艺术家作品,与此同时,根据主题方向,挑选非本画廊的艺术家和作品。大约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初步确定了展览的主题以及40余位拟参展艺术家的名单。展览最初的题目叫"反噬:与恶的距离",根据拟参展作品,将其分为"序曲:我会死的""美杜莎的诅咒""困兽""精炼的愚蠢""尾声:未来牧歌"五个部分。后来觉得主题稍显抽象,不够突出有力,遂改为"恶是"(Being of Evils)。
方案审核通过后,我和画廊分头行动,画廊联系他们自己合作的和个别他们推荐的艺术家,我负责联系其他艺术家。有几个艺术家的作品原本就在我的备选名单里,比如飞苹果的《下一秒》(2009),两年前在没顶公园的开幕活动中第一次看到,就一直想找个机会重展这件作品;还比如曹雨的《尤物》(2019)也很生猛,超出了她之前所有的作品;另如赵银鸥的绘画《2018. 2019. W》(2019),有一种难得的原始力,非常喜欢,等等。期间也有艺术家拒绝参展或中途退展,但并不影响展览的基本面貌,略感遗憾的是顾德新选择隐退艺术界之前创作的最后一组作品《2009-05-02》(2009)和朱昱吃6个月大死胎的行为摄影和雕塑作品《食人》(2000)因种种原因没能展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件作品可能更接近我的想法和展览的主题。至于主题"恶是"到底意谓什么,我在展览前言中已做过一个简要的理论说明,但这里还是有必要再重述一遍。
"人性本恶"的假定自古就有,中外思想家们还就此推衍出了一套又一套精致的道德哲学和社会治理术。可是,到底什么是恶,善与恶的边界到底何在,以及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不稳定的灰色地带和反转的可能性条件等,似乎并无一个亘古不变的说法和逻辑。
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柏拉图说,善就是正义。恶即非正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善恶取决于激情是否适度,以及是否被赞扬。很多年后,霍布斯对此予以了尖锐的批评,他断言:"使一个行为成为善的,不是激情的程度,而是行为的动机。使一个行为成为恶的,也不是激情的程度,而是因为对那些服从法律的人来说它不合乎法律的要求,或者它不适合在所有的人中实行公平或博爱。"[1] 因此他认为"合于目的的自我保存手段就是善",反之,"不合目的的就是恶"。莱布尼茨的论述则更为复杂,他将"恶"分为三类:"物理之恶""道德之恶"和"形而上之恶"。所谓的"物理之恶"指受苦受难,"道德之恶"即是犯罪,而"形而上之恶"则是一种本质上的缺陷。[2] 莱布尼茨在其著作《神义论》(Theodicy,1710)最后的分析中,以"形而上之恶"解释了所有的"物理之恶"和"道德之恶"。据此,一切痛苦、错误和罪似乎皆源于最初创世的不完美。[3]
然而,以上这些经典的论述却无法解释今天的现实。当灾难来临之时,我们其实无法区分"物理之恶""道德之恶"和"形而上之恶"。"物理之恶"可能来自"道德之恶","道德之恶"也可能源自"形而上之恶",还有可能转化成"物理之恶"。"合目的的自我保存手段"不见得全是善,也许是恶;并非所有的善都诉诸正义,有些恶也有可能是正义的......
有生以来,可能没有哪次灾难像这次疫情,让我们感到如此压抑、恐惧、愤怒和被剥夺的沮丧。但也正因如此,它逼使隐伏在生活角落中的一切"恶"浮出水面。艺术不是道德的化身,更不是正义之剑,违背常规的艺术很多时候反而与邪恶有关,甚至就是一种邪恶,然而,在这一时刻,邪恶不见得是真的邪恶,它兴许所代表的恰恰是善和正义;反之,那些打着正义旗号的艺术,或许才是真正的恶......就像霍布斯所说的:
善与恶是表示我们的欲望与厌恶的名词,在人的不同的性情、习惯和学说中,欲望与厌恶是互不相同的。不同的人不但对味觉、嗅觉、听觉、触觉和视觉所感觉到的愉快或不愉快的判断不同,而且对共同生活的行为是否合乎或不合乎理性的判断也彼此迥异。甚至对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赞扬它而称之为善,在另一个时候贬损它而称之为恶。[4]
展览无意弘扬正义,也无意发泄不满,无意反思人性,也无意劝人良善,而更加关心的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的混乱,彼此的撕裂,以及在某些人身上的颠倒等诸如此类的反常现象。"恶何以是,恶以何是,以及恶,何以为恶?!"此时,或许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问和深思的。
于是,我将展览分为"序曲:我会死的""美杜莎的诅咒""困兽""精炼的愚蠢""尾声:未来牧歌"五个单元。
"序曲:我会死的"源自杨振中的同名作品。杨振中的作品《我会死的》完成于2000年,它延续了1999年人们普遍的末世感。那一年,很多人觉得世界要灭亡了,地球要爆炸了。可没想到,20年后当疫情来临时,我们再一次感到末世将临,每个人都觉得,"我要死了","我会死的"。
第一单元"美杜莎的诅咒"源自陆平原的同名作品《故事系列-美杜莎的诅咒》(2020),根据这个神话,他虚构了一个同主题的故事,打开了这个单元。疫情肆虐之时,人们纷纷都在追问到底灾难的根源是什么,到底谁是"恶"的制造者,是人类自己,还是自然的自救,抑或其他?然而,后真相时代没有真相,只有层出不穷的信息,大多时候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逻辑,它可能是天生的,可能是长期累积形成的,也可能来自我们的一念之间。
就前者而言,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我们该如何面对庄辉"万物"系列作品(2006)、刘彦瑢"凉山风"系列作品(2020)中所昭示的那种原始的自然蛮力;人与动物的关系,比如徐渠《斑马》(2015)中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曹雨作品《尤物》(2019)中权力阶层的肆无忌惮[5],陈晓云的摄影作品《马勒隔壁》(2009)和张鼎影像作品《大时代》(2007)中的被压抑命运和泄欲式反抗;人与技术的关系,比如陆扬《子宫战士》(2013)、夏乔伊"木质结构"系列作品(2020)中关于未来技术与人的超自然想象;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王兴伟《无题(孪生)》(2007)中邪恶的镜像关系;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比如袁可如作品《会饮俱乐部》(2015-2016)中的忧郁、焦虑和狂欢,苏汇宇《屁眼·淫书·速克达》(2017)影像中的暴力、情欲、绝望与无政府幻想;等等。所有这些失调、失序,既是我们关于"恶"的追问,也是当下现实的隐喻。它们汇聚一堂,仿佛"群魔乱舞",彻底释放了我们内心的焦躁、忧惧、愤怒和歇斯底里,包括"丑陋"和"阴暗"。当然,并非所有的"恶"都是累积形成的,它也可能来自我们的一念之间,就像飞苹果的作品《下一秒》(2009)。
第二单元"困兽"想表达的是危机时刻被隔离的处境,同时也是现代人的命运。现代人一方面给自己建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另一方面又想冲破这个纵欲与虚无的空间。它可能是监狱、实验室、精神病院,可能是都市、网络、智能手机,也可能是金钱、欲望乃至资本主义体系。展厅中的U形空间,从内部看,它像一个人体实验室,比如宋陵《虚构 19 号》(2018)、徐震®《最后的几个蚊子》(2005)、郝量《躯之秘-2》《躯之秘-3》(2011)、宋琨"泛灵境界"系列作品(2018年至今)意在探讨身体是如何被理性化和机械化的过程和现实。谢南星的绘画嵌套在里面,像一个"转置空间",又仿佛一个孤岛中的孤岛。若从外部看,吕楠的系列摄影、赵银鸥的系列绘画、张鼎的录像作品《风卷残云》(2016)以及高磊"捕获器"系列装置作品《捕获器-人工智能》《捕获器-货币》(2017)、摄影作品《Building No.35-#333》(2006)都在暗示我们,它又像是一个精神病院或监狱。
而空间的四周,则被各种"病毒"和"邪恶"所包围,如于林汉所描绘的像"病源体"一样的不明物《与陌生共存2》《与陌生共存4》(2019),马文婷"坏东西"系列画作(2019)中腐烂的果蔬,李燎录像《怎样做一个**的人》(2018)中整容变形的直播女性,还有像邱瑞祥"无题"系列作品(2017-2019)中神秘而颇具魔性的农民,龚辰宇《偶像 - 维纳斯》(2019)画面中的人兽困斗,孔千《十梦寒食帖》(2008)、《演讲者》(2006)中异化的动物和人,等等。
事实上,"困兽"就是当代人的真实处境。因此在这个单元,我想把这个现实最大限度地暴露在大家面前。例外状态下,所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左边是地狱,右边也是地狱。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此时,人到底该如何自处?人与人之间又该如何相处?......艺术不是镜子,它就是活生生的残酷现实。
第三单元"精炼的愚蠢"源自于霏霏的同名雕塑《精炼的愚蠢》(2018),主要探讨人们在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所谓的理性反应。除了于霏霏的作品,这个单元还有像冷广敏、谭永勍、夏禹以及王音的绘画,透过他们的画面,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人类是如何理智地作茧自缚的,以及又是如何伪装自己的愚蠢的。
这个单元李怒为这个展览特别创作的一组装置《标准化感动》(2020)。它不仅虚构了一个被隔离、被悬置的危险处境,同时通过"沥青"这一物质本身也在暗示病毒的入侵,包括这样一个提炼物背后所投射的人类智识的野蛮及其不可控的反噬性。我援引了一段阿甘本在疫情发生后所写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这个单元的注脚,内容其实并不重要,我真正想说的是,像阿甘本这样的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在灾难来临时也可能会被"政治正确"所绑架,在那一刻亦会变得"无知"和"愚蠢"[6],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其实近一百年前,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提醒我们,真正危险和令人恐惧的不是理性与智慧,也不是疯狂和愚蠢,而是理性的疯狂和智慧的愚蠢。
这学期为研究生开设的课上,和他们一道重读李格尔的《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也联系到阿比·瓦尔堡,还有与之相关的尼采、韦伯、本雅明的文本。疫情之下,尤其对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和瓦尔堡的"情念程式"这两个概念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什么这些艺术史家、思想家会不约而同地着迷于狂热的意志与激情?百年后,身陷疫情和媒体漩涡中的我们感觉又回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期间,还撰写了一篇论文《艺术力—重识李格尔的"艺术意志"与瓦尔堡之"情念程式"》,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尾声部分"未来牧歌"中,包括段建伟、段建宇、田牧所构想的"未来牧歌",但同时也有陈荣辉系列摄影作品"空城计"(2017)、麻剑锋临时搭建的绘画装置《无题》(2014-2020)以及何岸的装置作品《何桃源》(2018)。展览的最后,回到蒲英玮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的新作《世界主义指示牌(牧歌)》(2020)。诚如作品所喻示的,我们都曾幻想人类大同,幻想有一天能实现共产主义,但同时我们又在制造着种种区隔、壁垒和暴力。这是全球化的一个隐喻,但同时,它也催生并加速了反全球化的进程。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们如何在废墟中想象一个新的世界,如何在绝望中想象自己的未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或许是最好的诠释,其中还透着一丝"新生"的期待:
这个光荣的时代要开始,正当你为都护,波里奥啊,伟大的岁月正在运行初度。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罪恶的残余痕迹都要消除,大地从长期的恐怖中获得解脱。他将过神的生活,英雄们和天神他都会看见,他自己也将要被人看见在他们中间,他要统治着祖先圣德所致太平的世界。......时间就要到了,走向伟大的荣誉,天神的骄子啊,你,上帝的苗裔,看呀,那摇摆的世界负着苍穹,看那大地和海洋和深远的天空,看万物怎样为未来的岁月欢唱,我希望我生命的终尾可以延长......[7]
2020年4月初,我将布展方案和设备清单传给了画廊。因为疫情,我无法前往北京进行布展,好在画廊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我并不担心。4月11日下午4点,展览顺利开幕,因为没法参加开幕,只好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览。原本以为疫情期间没多少人会前往现场,后来听说参加开幕的有300多人,超过了以往很多展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场地所限,加上布展公司尚未彻底复工,作为策展人,我又不在现场,所以最终的呈现还是和我原初的方案有一些出入。好在他们有现成的移动隔墙可以直接调用,省了不少工序和成本。不过,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展览不同于写作,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也没必要去建立一个清晰的线索,更多的感知和认识还是需要现场去体验,现场能否调动观众的情绪和感知是最重要的—尽管这对于当下来说是一个异常奢侈之举。
最后,还想重申的一点是,此次展览无疑是因应疫情的一个临时的艺术行动,但其并非直接针对疫情,或是某个地方、某个事件或某个(些)人,真正想探讨的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展览只是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写到这里,突然想起2019年年底回答《艺术新闻》"跨年声场"提问,在问及"对2020年的艺术世界,有什么样的期望?"时,我是这样说的:
十几年前,我们一直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极端事件频发的年代,很难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没什么可期待的,需要考虑的是作为一个当代艺术从业者,该以何种方式应对这些偶然的发生。[8]
一语成谶,没过多久,疫情便"不期而至"。这也提醒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是当代艺术的意义所在,也是所有艺术从业者工作的价值所趋。时至今日,疫情依然在疯狂地蔓延,病毒还在四处肆虐或在潜伏之中,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工作何时会回到常态,也许永远也回不去了,更无法预料未来还会发生什么灾难......然而,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们的行动并不会因此中断和终止。此时,"恶是"的效应还在持续发酵,而另一个同样因应危机时刻的展览"缪斯、愚公与指南针"(Engulf You!)也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当中。—[O]
[1] 艾莲·布希尤:《什么是恶?》,郭俊逸译,台北:开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第44页。
[2] 同上,第23页。
[3] 同上,第26页。
[4]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21页。
[5] 此作品后来在相关部门的审查中被要求撤下,主办方只好选择用二维码代替,观众可通过扫二维码在手机上浏览此作。
[6] 阿纳斯塔西·伯格:《阿甘本在新冠病毒上的无知和愚蠢》,吴万伟译。2020-03-29/2020-04-26。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634.html。
[7] 维吉尔:《牧歌》,杨宪益译。2010-07-02/2020-04-25。https://www.douban.com/note/78752015/。
[8] 《跨年声场@鲁明军:期待新的艺术出现,而不是消费别的领域已设定的议题》2020-01-13/2020-04-20。http://www.tanchinese.com/interview/52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