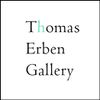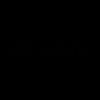杨福东:取景器前,显示屏后
杨福东在香格纳画廊举办的最新个展"无限的山峰"(展期:2020年11月8日至2021年1月24日),使我们恍然意识到其标志性的彷然、疏离的现代都市美学背后,一直蕴藏着的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探讨。

杨福东,《无限的山峰(一)》,2020。展览现场:"杨福东:无限的山峰",香格纳画廊,上海(2020年11月8日至2021年1月24日)。图片提供:香格纳画廊。
如果如杨福东所言,他关注的一直是中国的问题,那么此展中,这样的亲切与认同感首先体现在艺术家对于古代绘画范式、构图与主题意象的直接引用上——不但位于一楼展厅的混合了摄影和绘画两种媒材于一体的系列作品《无限的山峰(一)》《无限的山峰(二)》(2020)以垂直构图组成的长卷水平展开,于二楼展出的黑白摄影中也不乏似曾相识的山水画式垂直构图,如《无限的山峰—村口》(2020)等作品画面中三五成群的僧侣与道路沿途的小房子,更是依稀可见集会上谈笑风生的文人雅客和茅屋等经典绘画元素的影子。与此同时,在主题与隐喻的层面,展览所采用的复线叙事结构、虚实媒介并置的拼贴手法,也指涉了当下的多重现代性同存并行的现象。

展览围绕着"十六罗汉"这一绘画母题展开。罗汉是佛教中脱离生死轮回但仍常驻俗界、弘扬佛法的宗教人物,早在五世纪左右就已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七世纪玄奘的文化交流的推动下逐步在中土内陆得到普及。原本具有异域色彩的形象历经文化历史语境的几番变更,逐步呈现了世俗化且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本次展览所仿拟的两张分别出自元代画家颜辉与清代画家石涛笔下的绘画《十六罗汉图》(前者创作年代不详,后者创作于1667年)中均有所体现;数个世纪后,超脱俗界的佛性与田园牧歌的文人愿景再次不谋而合。
本次展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楼展厅主要呈现了以《十六罗汉图》为原型创作的长卷拼贴系列,而两楼则集中展示了以现代僧侣为题拍摄的一系列黑白影像作品,由艺术家近期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取景,以朋友演员为主角拍摄——如果说楼下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住世济人的圣人罗汉的想象,那么楼上则是艺术家对于这一信仰体系的当代续写与演绎;两条线索的分轨并行,时有交错。
穿梭在展厅中,观众被一种如影随形的自我意识所趋附,一方面,因为展览中设置了诸多具有互动性的观看细节。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一处是通往两楼的楼梯入口——艺术家将其巧妙地伪装成《无限的山峰(一)》长卷中的"一帧"画面,"穿梭门"的设置也为观众营造了"人在画中游"的奇妙体验。而在位于楼上的综合影像装置《无限的山峰(三)》展柜中,投影画面在观者的注视下出其不意地闪现,又消失,仿佛目光所及之处短暂地被声控灯点亮一样,与观众的一举一动存在着某种隐性的关联。
另一方面,这种心理氛围的营造也与随处可见的镜面有关。在处理一楼展厅中的绘画摄影拼贴长卷时,艺术家有意选择了镀膜镜面玻璃作为装裱材料,并通过调整镀膜张数来控制镜面反射的强度,整件长卷装置呈钢琴黑白键盘般的错落雅致。其中在《无限的山峰(一)》《无限的山峰(二)》中镀膜张数高达三张的几幅画面几乎无法看清玻璃面板后的绘画手迹,却也因此屏蔽了历史细碎的杂音,将映入画面的人影引入讨论中心。
艺术家将实景拍摄的竹林摄影置于手绘罗汉图长卷之中,画中描绘的场景仿佛残留于这片竹林的视网膜记忆,以某种时光闪回的形式再现。观众的倒影映在深得发黑的玻璃镜面上,也好似随即陷入了镜像中的世界。艺术理论学者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E. Krauss)曾将影像归为一种纯粹的心理媒介,而"自恋"(或字面意义上的"自我映射")即为这一媒介的核心作用机制。
从艺术家在取景器中捕捉的现实,到显示屏上出现的画面,两者间不存在延迟或改写,以镜面反射的方式实时共存、趋于相融。相应的,夹于两片镜面间的介质则构成了一个不断坍缩的空间,挤压掉最后一丝外在语境的阐释可能后,留下一个近乎真空的心理世界。
杨福东影像作品中出现的人们总仿佛困陷于这样的一个历史黑洞中,与外界存在着不可丈量的隔阂,而这些影像往往又都没有声音——真空中不存在传播声波的介质。如同《天色·新女性 II》(2014)中曾经举起海螺放在耳旁倾听的动作所暗示的那样,又或是艺术家在最早的《那个地方》(1993)的行为作品中所刻意营造的氛围。
展览"无限的山峰"在两楼的展柜装置中接近尾声,无论是投影画面中好似微缩模型的僧侣,还是意在诱发历史观看距离的博物馆式陈列方式,都进一步强调了展柜内外两个世界彼此间的隔阂。
取景器前,显示屏后,"无限的山峰"是杨福东的物理空间学。—[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