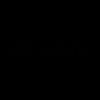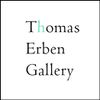表哥张书笺的几张近作
张书笺的近作[1]多是面部描画,却不见一张完整的脸。鼻子周围的皮肤(《通道》,2020;《通道2》,2020)被收纳进相框大小的画面,嘴巴眼睛都剔除。抑或,一只脖子,青筋暴露,上接咬牙切齿的牙齿,下接隐去不见的锁骨(《抬头》,2020)。人们走近,琢磨这些纤毫毕现的肖像:辨别不出谁是谁,又好像总是在哪儿邂逅过。一股熟悉的陌生感。
照相术发明后,对影像的修改没消停过,类似的陌生阴魂不散。英国人大卫·金写过一本《人民委员突然消失了——时代对照片及艺术的伪造史》(1997),讲斯大林将异己从图像纪录中清洗掉的往事。1920年一张列宁在广场上发表演说的照片上,托洛茨基和卡米涅夫正在演讲台下候场。斯大林掌权后,这一场景奇妙地发生了变化。木制的粗糙讲台将台下两位领导人的身躯吞没。肉体被处理后,生命于影像中持存。生命已然无法再关心自己作为信息还能发挥怎样功能,后方还有人跑来,对他穷追不舍,去抹煞已不存在的现实。"现实就是无法被表征的东西,而现实感就是那些正在挣脱表征话语的东西。"[2]图像存在于现实之外的什么地方,相较而言,它没完没了。
大概10年前,张书笺站在阳台,举起沉重的尼康D300相机,随手拍了张表弟的脸。那是个白天,光从阳台射进屋里,摄影师在表弟左眼瞳孔表面留下一个黑影,让人想起委拉斯贵支《宫娥》中的镜子。表弟的右眼斜向一边,躲开了张书笺的捕捉。大概10年后,张书笺偶然在网上看见一个斜视病例的照片。照片里的人长得凶悍,虽然斜视,但能逼视别人,虎视眈眈。他觉得他眼睛里的细节不够,翻出了表弟的老照片。张书笺画画,总是从眼睛画起。他开始画表弟的眼睛,然后画那凶残男人的脸。两张脸合成一张(《阳台》,2020)。他称这过程为"手工PS"。他这么一说,暗示着,现在,不仅尼康D300和网络替代了亲眼所见,图像编辑器也替代了亲手所画;暗示着,现在,他还坚持亲手所画,是由于执拗,是出于观念的需要。
两张"通道"和《抬头》又与《阳台》不一样。那些面部未曾被改动过,它们被精确地誊写下来,只是取景框停留在了别扭的位置。观众们走进"近作"的展厅,看到几块不曾定睛瞩目的皮肤。有些皮肤已经陈旧了,生长着像苔藓的色斑。皱纹从脸颊向四周蔓延开来,直到上扬的嘴角,直到耳根,像要漫灌进五官(《侧脸1》,2020;《侧脸2》,2020)。
褶皱霸道、切实,像是凿出来的,可它不是五官,无法定位出一个人的脸。肖像被发明伊始,要确保形象不朽[3];可那些皱纹告诉我们,不朽是徒劳。不过,张书笺没事儿还是会发发痴,想,若自己的画生生不灭永流传,就美好了[4]。—[O]
——
[1]:"快拍与动态——张书笺近作",CLC Gallery Venture,2020年7月18日至8月23日。
[2]:引自《艺术界LEAP》,2010年4月号,鲍栋,《张大力:第二历史》。
[3]:一般认为,最早对于个体形象的描绘出现在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这些描绘为死者保留形象,以便他们的灵魂找到依附的躯壳。历史学家布莱思蒂德(Breasted)把法老埃赫那顿在壁画和浮雕中的形象称为"世界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的个体"。
[4]:源自张书笺与杨紫2020年8月21日的微信对谈。原对话为如下:
杨紫:你想要你这些画永垂不朽吗
张书笺:想啊
杨紫:万一不行咋整 张书笺:那就不行呗,只是想想,谁都应该会想吧
张书笺:就跟想找个完美契合的对象,但几率太小了几乎不可能,所以只是想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