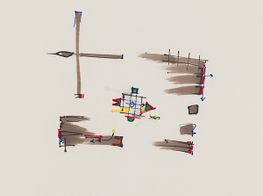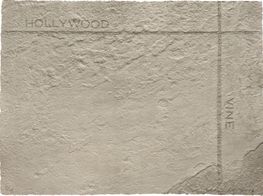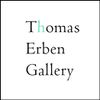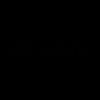拉斐尔·多梅内克:空间游戏
一切都是临时的:白墙的后面露出砖墙,从简易吊顶板的镂空中垂下电线,隐约透出内部结构,占据整个空间的、颇似建筑展上匆匆而就的模型展示平台。它们的存在和"不确定整体的不完美碎片"(展期:2021年4月22日至6月19日)这个摇摇欲坠的展览标题一样,已经暗含了易于且将会被拆除的命运。

展览现场:"不确定整体的不完美碎片",户尔空间,北京(2021年4月22日至6月19日)。图片提供:户尔空间。
拉斐尔·多梅内克(Rafael Domenech)将展厅变为一片拆除之地(land of demolition),这是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对纽约的形容——后者将对城市建筑的介入视作一种行为,一种生产公共空间和相遇场所的艺术尝试。而在户尔空间弧形切割的高迪式模型展示台上,多梅内克由现成品、被裁切、打孔的纸张和立体结构拼接而成的书恰似微缩建筑。它们以胶合板、鸡蛋纸盒、书皮布料等日常材料为结构,形成基座、屋顶等元素,相互镶嵌或接合。
然而在这个建筑结构内,图层、颜色和材料构成的却是没有深度的片面景观:艺术家往返工作途中的日常景象,配上标语化的硕大文字,似乎沿袭了创作艺术家书的先驱艾德·拉斯查(Ed Ruscha)的做法——拉斯查1963年出版的《26个加油站》(Twentysix Gasoline Stations)用无衬线的大字和乏味的公路纪实,冲击了当时摄影追求精致图像或人文批评的两重倾向——多梅内克的装置诚然是一种出版物,但其对排印学的尊崇远远盖过了书籍承载的信息。每一本书像是一件同样具有细小孔洞结构的丝网印刷品,以动态的三维形式存在。我们拨开一层层空间,让页面的孔穿过电线,翻阅,打开,折叠,近乎无意识的动作逾越了"阅读",更像是无目的、速食性的漫游。[1]
随着这些动作的展开,观众进入了艺术家的游戏。通过可互动的物品和需要穿梭其中的空间,多梅内克意图用将观众邀请进一个网中,构建促使人们交流并联结在一起的场域。然而,网是游动的,但并不总是友好的,甚至令人紧张不安,因为我们不是被空间包裹其中,而是被其分割:蔓延到展厅各个角落的平台上,散落的书将我们孤立在自身的体验里;灯光装置悬挂在视野的盲区,点亮了空间中往往不甚被注意到的、被遗弃的部分。这也意味着展览也难以被整体性地阅读或感知:从广告灯箱、书籍到建筑材料的交杂消解了展览可能的元叙事,强调的是对离散的拥护和对系统的质疑。在腾挪,游移和翻动中,整体被打破了,杂乱和无序四处矗立着。
当人们无论仰头看向天花板或者随光线蹲下身,都只能读到不连贯的语句,此时不安的体验同样进入了语言的层面:在展览中,语言几乎没有为图像和结构提供可被解读的释出空间,而是成为一种模棱两可的结构要素。无处不在的文字在被称作"诗歌"之前,首先以其纹样、色彩和节奏制造了一种排印学,与其它要素"相互冲刷"。(而展览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排印学实践?)而如若我们从其结构性回归到语义,便发现破碎的短句和展览标题一样充斥着否定:The plastic river has no corners(塑料的河流没有角落)There is no longer elsewhere(再无他乡)Things that amount to nothing(毫无意义之事)
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指出了语言的后现代状态:语言作为一种游戏,令我们在发话者、受话者和指涉物的角色间转换。语言在一来一回中产生位移,从而实现交流,而有效的语言游戏需要的不仅仅是反应,而是反击。[2] 然而,在多梅内克破碎的、否定的语言网络中,我们反击的余地被一再压缩。
2014年,奥巴马宣布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古巴现当代艺术的收藏热。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多梅内克从古巴移居纽约,以异乡人的身份(更甚,成长于另一政体下的异乡人身份)被抛入了英语语境中。诗歌原是一种将外乡人排除在外的文学,诗歌本身的结构特征使其跃过文学的间距,在不成整句的零碎词语中寻找一种不可言说或纯粹性,这一特征通常被视为母语者的共契。但在多梅内克这里,异乡人的诗歌也成为了一种捷径,它利用了间距的跨越。只是这捷径在中国——另一个非英语母语的异乡——付出了晦涩的代价。天花板上刻印的"A purposeful misconstruction of a small situation with no future (towards a bad infinity)"(在展览手册中被译为"没有未来的小境况的有意错置[通向糟糕的无限]")即是一例,试图跨越间距的通用语言在异乡的转译中显得有些笨拙。我们被艺术家安排了一个积极建构的角色,但究竟参与了什么?生产了什么?我们难以在发话者、受话者的角色间转换,只能局促地观望。[3]
于是我们放下建构的角色,像漫游者一样走在展厅里,这带来了另一种体验。诗歌语言在这个空间里无处不在,但艺术家却剔除了陈词滥调的对"诗意"的想象。恰相反,每一件作品都产品化,不同的媒介交织在一起,如同集合商店或是宜家样板间所营造的当代闲逛体验,意图使顾客迷失于其中。大型面板提供了一种新型、经济、实用的展示方式,"产品手册"置于其上,人们也得以一对一地检视与触摸"产品";激光切割的书籍、灯具、激光刻印的吊顶板,都极大地消除了手工的痕迹,精确得似乎随时可投入量产。在多梅内克过去制造的一些展示场景中,许多作品的确是可被使用的,或当作屏风和布景板,或当作椅子供人休憩。
当多梅内克用离散和异质取消了艺术品的阶级,这意味着艺术生产可以是一切。我们最终可以不把展览视作一个展览:在画廊的一角,艺术家的作品在茶歇间被当作功能性和装饰性物件,艺术空间与日常空间由此交融。这既是一张不安的网,一些动作的集合,也是一个商品展示室,一个生活居所。在如此的矛盾性中,我们反复被这个空间邀请,欺骗,排斥,接纳。—[O]
[1] 可移动的大型户外装置延续了展厅内的逻辑。在周围颜色单调但厚重的厂房建筑映衬下,一片片几乎没有厚度的弧形结构交错,呼应着包豪斯建筑的扇形屋顶,而这些用建筑防护网和脚手架搭成、叠加了高饱和色块、文字和孔洞的屏风更应和了北京的城市症候:一座不断在拆除和重建的城市,一座宣传的城市。
[2]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61-64页。
[3] 或许恰是因为与本地社群建立的这张网有些虚幻,展览以平行项目的方式,邀请在地艺术家介入、破坏、再生,从而实现某种更为亲近的语言生产。这再度弥合了此处的间距。然而只有艺术家才有反击的资格吗?